去年5月末權威人士發(fā)文不久,股市就引來6月的見頂回落;而1月4日再發(fā)文,當天股市又出現暴跌。這究竟是湊巧還是有所暗示,它們之間有沒有關聯性呢?
去年5月末,《人民日報》刊登了《五問中國經濟——正視困難 保持定力 前景光明》,時隔7個多月后,權威人士再度通過7問7答的形式發(fā)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tài)》。逐字逐句比較這兩篇前后相隔7個多月的大作,不難發(fā)現權威人士思維邏輯的一致性,以及由于經濟形勢變化,在應對之策上的不同點。
值得回味的是,5月末權威人士發(fā)文不久,股市就引來6月的見頂回落;而1月4日再發(fā)文,當天股市又出現暴跌。這究竟是湊巧還是有所暗示,它們之間有沒有關聯性呢?
權威人士有先見之明:防風險就是穩(wěn)增長
應該說,兩篇文章都是有感而發(fā),極具針對性和對大政方針的指導性。5月25日的五問五答,實際上是對4月30日中共政治局經濟工作會議的有感而發(fā),而1月4日的七問七答,則是對12月下旬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有感而發(fā),進一步厘清舉國上下對改革的認識。
4月末的政治局會議,最后推出了二季度穩(wěn)增長的“大招”,招式涉及降稅清費、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等投資、貨幣政策、擴大消費、房地產健康發(fā)展、創(chuàng)新驅動、國企改革、京津冀協調發(fā)展等八個方面。可見,大部分人對于經濟下行還是感到擔憂,會議采取八大招來穩(wěn)住經濟。但權威人士認為,“要高度重視應對下行壓力,但也不必驚慌失措。宏觀政策要保持定力,穩(wěn)字當頭”。“如果采取大規(guī)模強刺激和拼投資等老辦法,可能會積累新的矛盾,使包袱越背越重”。
權威人士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說,防風險就是穩(wěn)增長。當前經濟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仍要引起高度警惕。實現今年經濟發(fā)展預期目標,須把握好穩(wěn)增長和控風險的平衡,牢牢守住不發(fā)生系統性、區(qū)域性風險的底線。
結果,6月份股市出現大幅下跌,果然印證了權威人士的提醒。那么,按此邏輯,今年仍然是要防范金融風險的區(qū)域性或系統性發(fā)生。在金融步入混業(yè)化時代,股市的風險肯定是系統性風險,所以,高層應該不會容忍市場出現斷崖式下跌。今年股市應該是“有底的”。
“水牛”或將蛻變?yōu)?ldquo;改革牛”
權威人士認為,2013年中央認清了經濟形勢是“三期疊加”,明確了“怎么看”經濟,2014年提出“新常態(tài)”,實際上是明確了“怎么干”,2015年年末又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明確了主攻方向,以此推理,16年那就是一個字“干”。去年5月份,權威人士還告誡大家,不要心存僥幸,以為熬一熬經濟自然會起來。這次他更加明確地說,經濟走勢L型,改革的陣痛不可避免,改革的窗口期不會一直開著。要像98年朱镕基要求紡織行業(yè)壓錠那樣,斬釘截鐵處置僵死企業(yè)。
比較歷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會發(fā)現,過去提出的核心任務往往是大而全,缺乏可操作性。這次的五大任務: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和補短板,是非常具體和細化的,與去年5月的五問五答一脈相承,且當時他就提出要“注重精準滴灌”。所以,權威人士的改革思維應該也是注重“精準”,比如,歷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任務中,幾乎每年都提“結構調整”,他在5月份雖然也提調結構,但同時又提“結構調整是新常態(tài)更本質的特征”。這也就是這次重點談“供給側結構化改革”的原因所在,因為只講結構調整比較籠統,與之前的提法沒有太大差異,各級政府部門不一定會高度重視。
其實,在5月份的文章中,通篇只有一處提到“供給”一詞: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是可觀的,一個黃金周就能在境外刷新人家的銷售紀錄,關鍵是我們要有令人心動的有效供給,有讓人心安的產品質量。可見,他是從當初淺層次的供給入手(這也是很多國人的直覺,認為國內產品質量不到位,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行,如到日本購買電飯煲和馬桶蓋),提出要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目標的供給側改革。
那么,對股市而言,又有哪些相應機會呢?去年股市的機會主要來自于央行降準降息,實體機會少導致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和加杠桿,所以屬于“水牛”。如今,權威人士提出改革要做加減乘除,故機會主要集中在加和減兩個方面,如化解庫存是加法,對諸如房地產庫存較高的地方或有投資機會;而今年固定資產投資中的那些增量最大的行業(yè),也屬于加法,如政府投資較大的交通設施、民間投資熱衷的IT、傳媒、醫(yī)藥養(yǎng)老等高成長行業(yè)。減的方面,機會主要是去產能,權威人士倡導多用并購重組的方式來處置僵死企業(yè),這就意味著國企改革、并購重組板塊的機會依然較大。
2016年大盤藍籌股的機會大嗎?從估值角度看,其泡沫化程度較低。但根據權威人士的建議,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絕不要隨便放水,各地區(qū)各部門不能“放水漫灌強刺激、盲目擴建新城區(qū)”等。這意味著16年的投資增速依然會有所下降,周期性行業(yè)的復蘇遙遙無期,去杠桿、去產能,處置僵死企業(yè),將使得銀行的信貸規(guī)模難以提升而壞賬規(guī)模則會顯性化。這就意味著大藍籌沒有業(yè)績浪的支持,反而有業(yè)績下行的壓力。
對于中小市值股票而言,PE普遍偏高,盡管題材和成長機會較多,在去杠桿的大背景下,投資者的預期回報率水平也會下降,且新股的供給也將增加。所以,16年的股指要期望大漲也不現實。只能是結構性的機會。
改革能否取得預期成效
回顧過去10多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每年都提改革任務,但進度和成效似乎不太明顯。對此,權威人士也做了回答,提出要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幾個重大原則,認為政府要“更好發(fā)揮”作用而不是“更多發(fā)揮”。比較這兩篇文章,感覺權威人士的經濟學理論確實有其獨到之處,供給側結構化改革的概念與一些學者提出來的所謂西方供給學派理論沒有多少相關性,倒是可以看到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一些蹤影,如“產業(yè)政策要準”,政府的作用等。
目前的難點在于執(zhí)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結局往往是從問題導向變?yōu)槔鎸颍瑥囊愿纳瀑Y產負債表為目標,變?yōu)橹唤鉀Q現金流量表。不過,好在當經濟不斷下行,日子過不下去的時候,改革的推進將是“問題倒逼、必進關口”。
兩篇文章對比,可以看出,權威人士對經濟形勢的判斷能力和認識水平顯然是高于其他人,如果說,5月份的那篇是在爭議中推出,那么,1月4日的這篇則更像是共識之下吹響了改革號角,應該值得投資者期待。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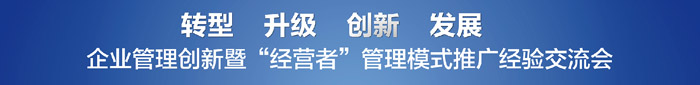
.bmp)

.bmp)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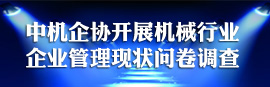

(3).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