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5日報道,生態(tài)環(huán)境部4日集中約談重慶石柱、廣西玉林和江西宜春等3市(縣)黨委或政府主要負(fù)責(zé)同志,要求認(rèn)真對待中央環(huán)保督察整改任務(wù),嚴(yán)禁表面整改,敷衍應(yīng)對,得過且過。
惹得生態(tài)環(huán)境部如此“震怒”,當(dāng)然是因為上述三個地方存在“表面整改”問題。嚴(yán)禁“表面整改”,當(dāng)然不能只有“震怒”和斥責(zé),還得有讓應(yīng)付檢查者能感受到“刺骨之痛”的懲戒措施。
為什么會存在“表面整改”,需要深思。應(yīng)付檢查,搞“表面整改”,不能簡單斥之怠政或瀆職。“表面整改”的原因,可能是基層干部和工作人員不把檢查當(dāng)回事,以為走走形式,應(yīng)付一下就可以過關(guān)了;也可能是地方政府舍不得一時一地的短期利益或政績,弄虛作假;還有可能是整改任務(wù)太艱巨,地方政府實在無法完成。盡管“表面整改”是不對的,但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嚴(yán)禁,可能效果并不如意。深究細(xì)查“表面整改”的深層原因,是需要加強頂層設(shè)計完善督查工作機制時應(yīng)該予以考慮的。
嚴(yán)禁“表面整改”,必須有切實的懲戒配套機制。被約談的地方政府,都有明顯的“違規(guī)”。據(jù)《人民日報》的報道,生態(tài)環(huán)境部措辭嚴(yán)厲,指出廣西博白縣在對那林自然保護(hù)區(qū)確界時,擅自將大面積生態(tài)公益林和天然林調(diào)出保護(hù)范圍,擬使該自然保護(hù)區(qū)面積削減87.7%,消極應(yīng)對中央環(huán)保督察整改要求,性質(zhì)惡劣。發(fā)現(xiàn)執(zhí)法中的問題,是督查工作的前半段,發(fā)現(xiàn)問題后,相應(yīng)的懲戒機制迅速跟上,應(yīng)該是督查工作的后半段。要知道,報道披露的不是首次督查發(fā)現(xiàn)的問題,而是對中央環(huán)保督察交辦問題整改不力。為此,有必要追問兩個問題:一,為什么個別地方在被中央環(huán)保督查組首次指出問題后,敢于在“表面整改”上下功夫?二,如果還有地方在嚴(yán)禁“表面整改”后,繼續(xù)應(yīng)付,該怎么辦?能回答這兩個問題的,只能是配套的懲戒機制。
要把嚴(yán)禁“表面整改”落到實處,就需要在頂層設(shè)計上主動發(fā)力。如果只把環(huán)保督查當(dāng)做環(huán)保部門一家的職責(zé)來看待,從環(huán)保部門一家的角度來設(shè)計督查工作機制,就可能面臨“你說你的,我干我的”尷尬。從發(fā)現(xiàn)問題到督促整改,從落實懲戒措施到推動整改到位,需要有各環(huán)節(jié)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嚴(yán)密系統(tǒng)思維。由環(huán)保部門承擔(dān)實施懲戒的主體,顯然不現(xiàn)實。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立足“大環(huán)保”,做好頂層設(shè)計。比如,在開展督查時,不妨引入人大監(jiān)督力量,使執(zhí)法檢查、問題督查更有權(quán)威性和約束力。在懲戒機制設(shè)計時,引入監(jiān)察部門和組織部門,在制度設(shè)計上使監(jiān)察部門和組織部門成為落實懲戒措施的責(zé)任主體。
任何一項督查工作,都不能“槍里沒有子彈”。中央環(huán)保督查組提出嚴(yán)禁“表面整改”,需要相關(guān)部門“全面武裝”,落實懲戒,讓挑戰(zhàn)禁令者切實感到痛感和“失去感”。(鄭博超)
- 王瑞祥主持召開中機聯(lián)黨委常委會 學(xué)習(xí)貫徹落實中央精神研究部署有關(guān)工作
- 中機聯(lián)王瑞祥會長主持召開網(wǎng)上視頻辦公(擴大)會
- 中國電器工業(yè)協(xié)會公開信:堅定信心 齊心協(xié)力 打贏新型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
- 中機聯(lián):關(guān)于共同做好疫情防控與企業(yè)有序復(fù)工復(fù)產(chǎn)服務(wù)工作的通知
- 2020年中機聯(lián)專家委新春座談會以通訊形式按時召開
- 中機聯(lián)倡議書:堅定信心 攻堅克難 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zhàn)爭
- 凝心聚力,并肩作戰(zhàn),共同打贏新型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
- 新能源汽車有望占比25% 未來純電動仍是核心方向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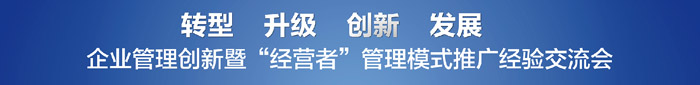
.bmp)

.bmp)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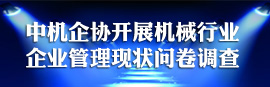
題-2.jpg)
(3).gif)
